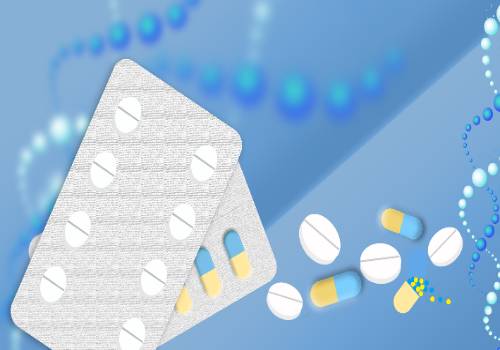王宗仁,著名军旅作家
您14岁就发表散文,童年时期的阅读是怎样的?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王宗仁:我记得是上初小四年级时,我常常给村里的大人们读报纸,能看到的是《陕西农民报》,田间地头,村口麦场歇息时,社员们就坐在场边树荫下,听我念报上的消息。村里的胖子三爷很喜欢我,说这娃勤快,会有出息的。他常常给我讲村里和邻村发生的故事。我的作文就记下了这些事情,老师表扬我写得不错,作文课上就作为范文给同学们念。这个老师叫乌安民,偏爱我。一次我在乌老师办公室看到《陕西日报社》给他寄的信,厚厚的。我很好奇就打开看了,原来是一份退稿,题目是《算黄算割又叫了》。这么好的题目!我偷偷记下了报社的地址:西安市中山大街166号。《陕西农民报》也是这个地址。
我就这样开始给报社投稿了,把作文上三爷讲的故事写得详细一些,投给报社。《陕西农民报》或《陕西日报》。是通讯还是消息,我也分不清。这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,村里有个我叫堂兄的青年表现得很好,写了多次入团申请书,却入不了团。我便写了篇文章《他为什么不能入团?》,投寄给《陕西农民报》,没想到报社把这份稿转给省共青团委员会,他们派人来调查,解决了问题。我的写稿积极性大增。
我的文学处女作应该是散文《陈书记回家》,发表在1959年第8期《陕西文艺》上,写的是我们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娶了媳妇忘了娘。这种养儿不孝的事在当年的乡村总会见到,我当时正读小学六年级,暑假时回到家里听到这件事心里打抱不平,就写了稿子投给《陕西文艺》月刊,次年我考上了县里初中,文章发表出来,当时在学校影响很大,语文老师专门找我了解情况,介绍我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。
那些年我在乡间读不到什么文学书,主要读三种报纸:《陕西日报》《陕西农民报》《陕西青年报》,我是村里的读报员,报纸都在我家里存放。1957年我入伍前,在《陕西日报》“秦岭”副刊发了三篇散文:《赵大爷》《两麻袋玉米棒》《离娘的骡驹谁喂大》。
启蒙老师有哪些?在阅读上,有谁对您予以引导吗?
王宗仁:启蒙老师除了上面提到的乌安民,还应该有上初中时的语文老师王瑞祥。他是从西安城里下放到乡村的左派分子,他组织了个文学社,教我们写作文。我从他那里看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,学习写作长进不少。后来他退休后在法门寺摆地摊卖杂货,我从北京休假回家还专程看望他。再后来他平反后回到西安,晚年患了老年痴呆症,我们还有电话联系。虽然他已经不记得我了,我仍然常给他打电话问候。
有人说十八岁之前的经验足够一生的写作资源。但是您离开青藏高原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几乎每年都要从北京去一次青藏高原,是创作需要还是心系高原?这种紧密的联系,对您创作有怎样的影响?
王宗仁:对我,十八岁不行。不要说够一生的写作资源,十八岁那年我才刚开始步入真正人生的门槛,青藏高原的第一个台阶日月山。真正使我有了一生写作的资源是在青藏高原的七年生活。可以说那七年我把这一生的苦都吃了,足够我一生品尝。但是光吃苦不行,还得从苦中跳出来,找乐,苦才能变甜,先苦后甜。否则,吃的苦越多,成了苦海,会把你淹死在苦海里。甜,就是要有理想,有了理想就有了跳出苦海的力量。支撑我跳出苦海的力量就是文学创作。
我每次上青藏高原,一成不变的行程要到昆仑山下的烈士陵园去祭奠,看望掩埋在这里的八百多名高原官兵,他们都是在和平年代献身于保卫边疆的英雄。我要特别在曾经和我一同战斗过的战友、乡友的墓前说一段祝愿他们的英灵在另一个世界安详、美好的话。
您的写作基本上是无师自通,自学成才?在部队的生活很苦,是什么支撑您不停地写下去?
王宗仁:二十来岁的小伙子,开着汽车哪一个月都要在世界屋脊上奔驰好几次,满身有用不完的劲。写作也是这样一股闯山的劲头,一心想着当作家,写了好多稿子,哪怕偶尔刊登一篇,伴随而来的是不可言说的满心喜悦。有时遇到大雪封山,铲雪开路不知要付出多少体力,我一边挖雪开道一边在心里就衍生出文章的细节,处于亢奋状态。我甚至庆幸自己能遇到这样的事,又有可写的题材了。1959年我写了一篇小故事《风雪中的火光》,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,是新闻联播之后的《解放军生活》节目播发的,我们那个小村里的人都听到了,写信讲这件事。这种鼓舞力量在那时是很巨大的!
您的军旅生涯长达59年,不同时期,您的阅读是否也有不同特点?是否对军旅文学的阅读也有所偏好?
王宗仁:我调到北京之前,在高原汽车部队开车,对刘绍棠的小说简直喜欢到骨子里了,只要能买到他的作品,比如《山楂村的歌声》《运河桨声》等,我都反复读,当地书店买不到,我就通过新华书店订购。后来刘绍棠成了“右派”受到猛烈批判,我心疼了好久。我对李瑛的作品也十分喜爱,他的诗集我几乎都买了,后来买了他的文集。我写散文诗应该说是受他的影响。还有苏联作家肖洛霍夫《一个人的遭遇》《静静的顿河》我也反复阅读。我后来创作的散文《情断无人区》就是受他的作品影响。
您有枕边书吗?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?
王宗仁:一直到现在,就是回答你的提问时,我的手边还放着《静静的顿河》,那个叫葛利高里抽着鞭子使劲催着战马驾着车撒欢儿的样子,还活灵活现浮现于眼前。我很喜欢这个不同凡响的人物。
哪些书是您一读再读的?
王宗仁:说起来读得最多的书还要数杨朔的散文《雪浪花》、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。后者我尤其是翻阅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有收获。他在作品里表现出来高超的艺术技巧,塑造出来的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物形象,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细微活动变化,耐人寻味!
您有怎样的阅读习惯?喜欢快读还是慢读?
王宗仁:我习惯躺在床上把枕头垫得高高的,半躺半坐着读书。右手拿着笔遇到我十分感兴趣的段落或句子,就划出来,有时还抄下来。回过头再读。这是品读,能读出味道来,好像尝到一席特色菜,沁入到心肺里了!
您的散文《藏羚羊跪拜》被选入六年级(预备年级)第一学期语文课本第19课(上海版)等课本。您会经常参加讲座,对学生或部队官兵谈自己的阅读人生吗?会给他们推荐书目吗?如果推荐,会是什么样的书单?
王宗仁:除了《藏羚羊跪拜》,我的另外两篇散文《拉萨的天空》《夜明星》也都被选入了课本,其中《夜明星》在20世纪90年代初选入全国通用的初中语文三册,现在六十岁左右的人在初中时都学过。记得《藏羚羊跪拜》在央视董卿主持的《朗读者》由陆天明朗诵后,一夜之间我的名字走进千家万户,那一夜我家的电话几乎打爆了,都是祝贺的文友或读者。
令您最受益的书是什么?对您来说,写作的魅力是什么?
王宗仁:最受益的书除了上面提到的外,还有李瑛的诗,我买了他的文集,通读了好几遍。李瑛说诗歌让他变成了孩子,我也深有此感。我多次当面聆听他的教导,太有收获了。我的散文诗集《雪山壶中煮》就是自己学习诗歌写作后陆续创作的作品。我偏爱这本书,不久前青海人民出版社又重印了这本诗集。
如果有机会见到古人,您想见到谁?希望从他那里知道什么?王宗仁:李白。
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,您会选哪三本?
王宗仁:除了我在上面提到的任意两本外,还想带上我的散文集《藏地兵书》。除了这本书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外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书中写到的青藏高原驻守的官兵外,还有一位早早就献出生命的“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”。他是在国家尚未计划修建西藏公路时,自己组织民工带着两千匹骆驼修起了这条路。跨越世界屋脊的2400公里公路呀!彭德怀元帅在视察了昆仑山下的部队时,称赞慕生忠是“青藏公路的先祖”!(主持:宋庄)












![[PC]:PC市场一周前瞻_天天热点评](http://img.qipei.nancai.net/2023/0612/20230612033107198.jpg)